
郑智化在2025年经典时光群星演唱会•汕头站上演唱。图/CNSphoto
记者|仇广宇
一位歌手站在舞台中央,最初,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谁。但当他开嗓唱出“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”的时候,所有的目光都向他集中而去。寒风里,人们的记忆像被突然唤醒,激动地站起身,大声跟唱起“风雨中,这点痛算什么,擦干泪不要问,为什么”。
即便已经过去三十年,无论在任何地方,只要郑智化开口唱起《水手》或《星星点灯》,一定能引发这样的合唱。作为三十年前就风靡华语地区的中国台湾歌手,人们常用“传奇”“励志”这样的词语去形容他。他确实传奇,身体不便,又从未系统学习过音乐,却在红男绿女的娱乐圈成为顶流,但说他励志或许更多的是误解,无非是因为他传唱度最高的两首歌《水手》和《星星点灯》的意象衬托着郑智化本人的身体状况,让歌迷想象出一幅悲壮的图景。但“励志”这个标签,他自己从来未曾接纳过。

郑智化传唱度最高的两首歌之一《星星点灯》。
真正的歌迷会知道,郑智化的底色绝不是“励志”和“传奇”所能概括的,他是华语乐坛少见的人文歌手,在热门作品之外,他曾写过直面矿难的《老幺的故事》,也写过《堕落天使》《三十三块》这样揭露社会问题、关注社会角落的作品。只是这些“冷门”歌曲,被淹没在他那两首太过著名的旋律背后,仿佛一盘老式磁带的“B面”。
这些年,郑智化只在一些演出中露面,也举办画展,研究书法,偶尔发首单曲。2024年10月,已经二十多年没推出专辑的他,出版了一张全新专辑,取名为《不思议》。其中的歌曲,算是他这些年来的一次集中表达。
他似乎依然无法真正沉默。正如他在新专辑中那首名为《哑巴的歌》的新歌中唱到的那样:“有些话积攒太久,想要说却写不出歌。真的声音乏人问津,为了成名必须矫情。也许我已经沙哑,只能自己对自己说话,渐渐地越来越结巴,终于变成了一个哑巴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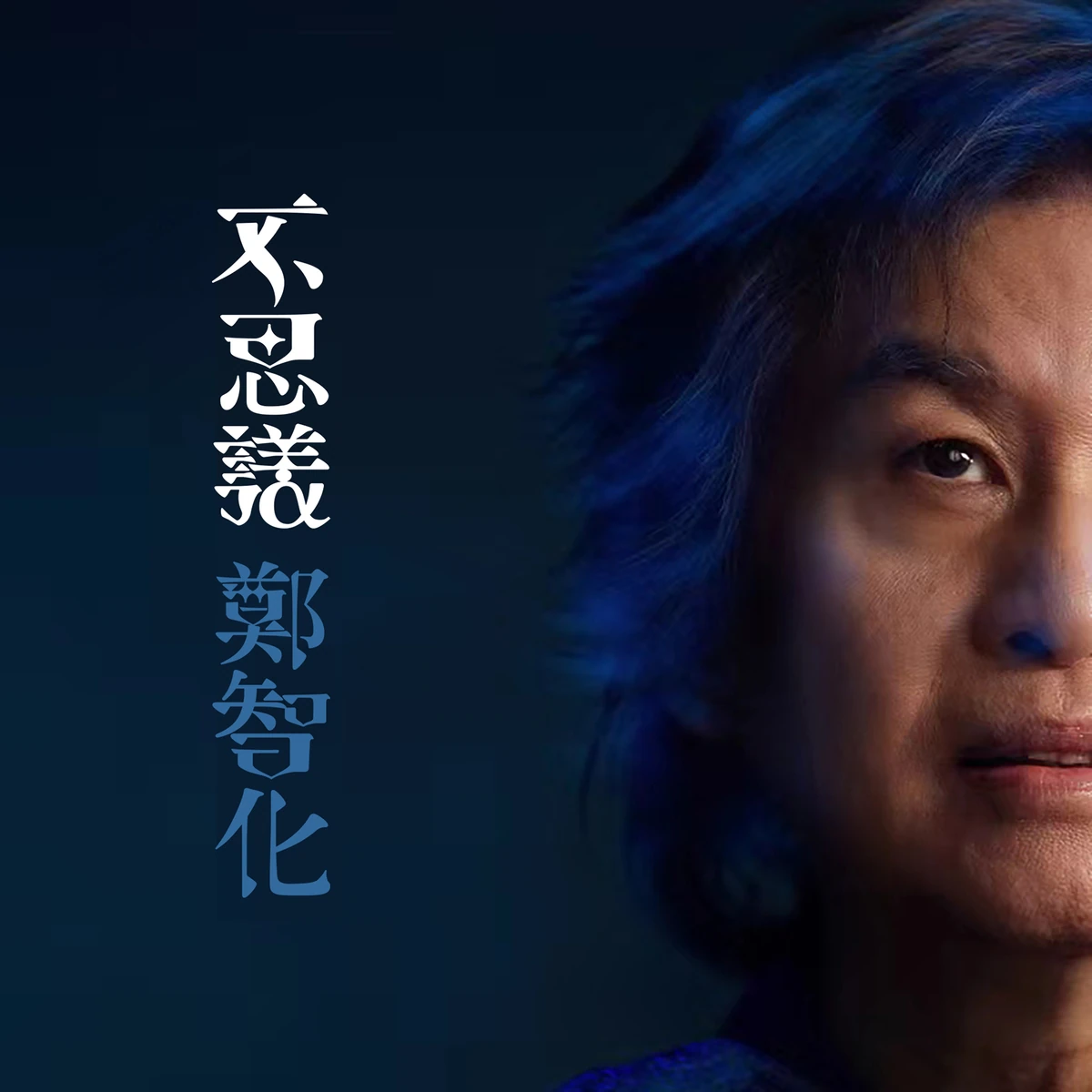
2024年郑智化全新专辑《不思议》。
言之有物的“杂食动物”
近些年,每隔一两个月,郑智化会来大陆工作几天,只是不一定每次都是以歌手的身份。2024年12月19日,郑智化出现在大连,出席个人画展“溺爱”的开幕式。画画、书法、做漆器……实际上,做这些事对郑智化而言并不算是“跨界”,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和音乐为伴的人。因为从小腿脚不便,不能经常出门,少年时期,他一直在家画画、写书法,读各种书籍。这让他变得兴趣广泛,像个“杂食动物”,涉猎一切。
他对待音乐的态度也是如此,“自己的见解”几乎是他此前所有作品的特征。正是因为能超越从前的自己,他等待了很多年。“其实二十多年来,我每天都想出新专辑。”他笑着说,他当然知道哪些音乐做出来社会反响会好,可就不想这样随随便便地做,结果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。不过,令他没想到的是,疫情期间,有大段时间关在家里,灵感居然如同泉涌,顺畅地写下了不少歌曲,最终,其中的十首歌集合成为《不思议》。他感到十分惊喜。“我只能说,年轻时,你就算拿枪顶着我,给我几百亿,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。”他对记者说。
他自我剖析,年轻时,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极为浓烈的情感。但如今,新专辑《不思议》中的歌曲似乎显得平和宽容许多,棱角更少,视角更宽。确实,在新歌中,郑智化擅长的那种叙事性极强的个人故事少了很多,如今的他,更多地用诗一般的语言,用“狼”“狐狸”“猎鹰”“哑巴”等作为喻体,曲折地表达他所看到的世界。

1992年8月,郑智化参加央视“92圣火”晚会,演唱《水手》。图/视频截图
磁带的A面与B面
郑智化几乎是一夜成名的。
那是在1992年8月,一场名为“92圣火”的奥运主题晚会正在筹办,郑智化也应邀来到北京录制节目,演唱他新专辑中的作品《水手》。那时传播渠道有限,一些大陆听众在磁带或者电台中听到过郑智化的歌曲,却没机会见到他本人,甚至有人推测,他可能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大胡子歌手。当年轻斯文、拄着拐杖的郑智化突然出现在荧屏上,用凄凉的嗓音唱着“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”的时候,人们才看到这个台湾青年真正的样子。那一晚,在直播中,数以亿计的观众被他歌里的真挚深深打动,在这样的舞台上,他的身体状况、才华与永不放弃的奥运精神被联系在一起。他开始迅速走红。一年之后,在央视35周年的台庆晚会上,赵丽蓉、郭达和蔡明在表演小品《追星族》时,郑智化这个名字显然成为当时的“顶流”代言者。
那时,大街小巷都是《水手》和《星星点灯》的旋律。这两首歌代表了“A面”的郑智化:一个坚强勇敢、能够以歌声给困境中的人激励的坚强灵魂。不过,也总有一些敏锐的听众,从那时起就发现了郑智化的另一面。《不思议》专辑的执行制作人崔轼玄生于1978年,他记得,20世纪90年代初,读小学要升初中的他,偶然看到了一句被刻在书桌上的话:“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,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。”他顿时觉得这句话写得像诗一样美。过了很长时间,他才知道这句话是郑智化的《让我拥抱你入梦》中的歌词。从那时起,他开始买郑智化的磁带,并痴迷于他作品中文字的力量。后来,在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《水手》的歌词中,在“这点痛算什么”的表象之下,他也听到了“都市的柏油路太硬,踏不出足迹”这样批判式的表达。
20世纪90年代初,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在中国台湾,那时市场上情歌当道,偶像组合也开始崭露头角,街上的人要么沉浸于《青苹果乐园》的愉快和青春,要么就是在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这样的伤感情歌里伤春悲秋。虽然当时的一些流行音乐还保留着“民歌时代”的人文色彩,但更多的作品还是表达风花雪月。
作为郑智化的前辈,以及同样擅长社会观察的知识分子歌手,罗大佑的巅峰创作期已经过去了。因此,几乎只有戴着墨镜,一脸不忿的郑智化一个人保持了犀利的棱角。他用电影镜头一般的视角,直白沧桑的嗓音和叙事诗一样犀利、深刻的歌词,不停地表达着他对社会的疑问和看法。郑智化的歌词创作,涉猎的范围极为广阔:当时最热门的高房价问题,“中产阶级”的生活问题,股市暴涨暴跌的问题,都在他的歌中有所体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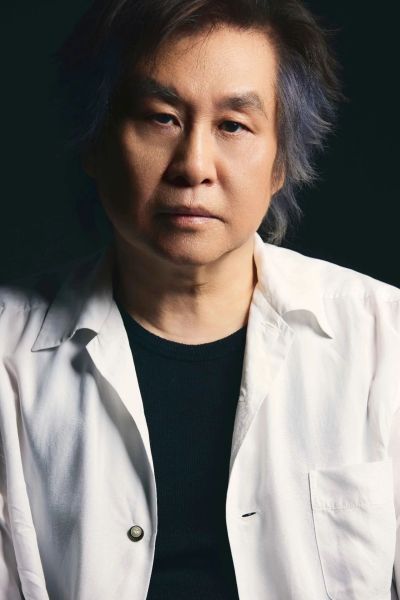
郑智化近照。图/受访者提供
除了讽喻、批判和省察,郑智化对芸芸众生也怀有一种深深的悲悯。矿难遇害者的家属、满怀理想却穷困潦倒的都市人,都是他书写的对象。难得的是,成名后,他依然继续在街巷中行走、观察、写作,或嬉笑怒骂,或深深共情。这样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探索,也存在于《阿飞和他的那个女人》《未婚爸爸》《堕落天使》等很多作品之中。
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,多少和郑智化童年的创伤有关。他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,7岁时动过一场大型手术,在医院康复时,最难受的时候,感觉“心脏像被几万只蚂蚁一口一口咬”。身体好转后,他的人生逐渐顺遂,但曾经的痛苦,也为他种下了一颗超越常人的同理心。于是,在郑智化1988年有机会出版第一张专辑的时候,他就不自觉地把目光对准经济腾飞的社会下那些弱势、没有话语权的人群。
实际上,对郑智化而言,当他写下这些歌时,他无法判断究竟哪一首能够走红。他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而已。不过,有了那些被广泛传唱的“A面”歌曲的帮助,那些留在“B面”的冷门歌,还是收录在专辑中,与知音们安静地相遇了。
20世纪90年代中期,华语歌坛日益偶像化、商业化的趋势,使坚持严肃表达的郑智化似乎感到更加寂寞。到了1998年,推出一张名为《夜未眠》的专辑之后,郑智化真正淡出了歌坛。
如今,“重出江湖”的郑智化清楚,音乐人或许面对着一个更加残酷的市场,得拼命去和游戏、短视频争夺人们的体验与稀缺的时间。他一边担心这样粗糙的环境只会生产出劣质的口水歌,另一边也明白,流量时代不可逃避。渐渐地,他也发现了一些流量所带来的正向作用。那些旧日里富有深意的老歌,曾经被埋没于流行之声背后的B面作品,反而借着流量的东风被一点点重新发掘,它们在互联网上被反复点击聆听,获得了更年轻的听众的支持。在一些音乐软件上,不少“00后”开始留言,称自己听懂了郑智化老歌中的深意,并感叹那个音乐作品璀璨争艳的时代。让郑智化没有想到的是,他在63岁出版的这张专辑《不思议》,不到一个月就卖掉了几千张实体CD。这个数字在实体唱片几乎消亡的如今,算是一个如专辑名称一样“不可思议”的成绩。
这或许算是一个良好的预兆。正如郑智化在《哑巴的歌》中唱到的那样,他自以为已经“乏人问津”的声音,还是有机会,在网络时代、短视频时代的某一个莫名的瞬间,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,重获新生。

(本文由中国新闻周刊相关文章改编而成,已获授权,内容有删减,如需了解更多信息,请扫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信二维码。)
